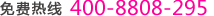
?
目前己知最早的譯作為1941年6月、張愛玲21歲時發(fā)表于《西風精華》第6期上的《謔而虐》,選譯自1938年美國暢銷書With Malice Toward Some。《西風精華》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西風月刊社系列刊物中最晚出的一種。第一種為著名的《西風》,于1936年9月創(chuàng)刊,以“譯述西洋雜志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為辦刊宗旨,主要撰稿人包括林語堂、老舍等名家。創(chuàng)刊于1940年的季刊《西風精華》旨在“譯述西風精華,介紹歐美讀物,對西洋文化作進一步之介紹”。其撰稿人也是名家眾多,以張愛玲發(fā)表《謔而虐》的第6期為例,就有《西風》創(chuàng)辦者之一黃嘉德、廈濟安和喬志高等。張愛玲的譯作能在此期刊上公開發(fā)表,也證明了張愛玲的翻譯實力。
1952年夏至19”年秋,由滬至港的張愛玲主要靠翻譯工作維持生活。她為美國駐香港新聞處翻譯了一些美國文學名家名作,先后譯有勞林斯《鹿苑長春》、《愛默森選集》、海明威《老人與海》、《美國詩選》(合譯)、《歐文小說選》(合譯)、《美國現(xiàn)代七大小說家》等。在這些作品中,張愛玲最喜歡的是《老人與海》,她在1954年11月為中譯本作了一篇稱得上飽含深情的序言,表達了對該作品的欣賞和喜愛。她極少給這一時期的其他譯作寫序,除了《愛默森選集》,但是后者的序言雖然比《老人與海》的譯者序長很多,但摹本上是對愛默森生平創(chuàng)作和主要思想的介紹,對翻譯方面的心得體會只字未提。這與宋淇(著名翻譯家林以亮的筆名)的回憶是一致的.據(jù)《私語張愛玲》介紹,“張愛玲其實對她翻譯的這些美國文學作品都不喜歡,無可奈何地硬著頭皮譯,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老人與海》”。
張愛玲自己曾說過:“我逼著自己譯愛默森,實在是沒辦法。即使是關(guān)于牙醫(yī)的書,我也照樣會硬著頭皮去做的。”這一方面反映了作為作家的張愛玲在那段非常時期不得不以翻譯為主業(yè)的無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譯者的張愛玲在譯自己不喜愛的作家或不擅長文體時面臨的巨大困難。不過,這些狀況并不能說明張愛玲在港期間的譯作,除她自己推崇的《老人與海》外,都是沒有價值的。張愛玲對超驗主義的兩座豐碑—愛默生與梭羅在中文讀者中的譯介具有開拓之功。事隔多年,1986年12月,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張愛玲所譯的《愛欺森文選》,仍有學者對其作出如下評價,“由于譯者本人就以從事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而著名,因而在翻譯時能很好地抓住原作的神韻,整個譯文讀來有很難得的順暢舒服之感”。仔細閱讀她這一時期的譯作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張愛玲不僅是一個認真寫作的作家,同樣也是一個負責的譯者,她利用自身的語言天斌,為我們奉上了這些美國名著的初譯本,其中絕大部分到今天仍稱得上是原著最好的譯本之一。
后來她對創(chuàng)作作品進行自譯。《秧歌》和《五四遺事》都是先出英文版再自譯成中文的。《怨女》被公認為是張愛玲英語創(chuàng)作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中文版,其正式出版雖然晚于后者,其實是根據(jù)后者翻譯而成的。《赤地之戀》則正好相反,先寫中文再譯為英文。以上作品的中英文版本都是正式出版或發(fā)表的。1961年,她把《桂花蒸•阿小悲秋》節(jié)譯成英文,收進聶華荃編譯的《中國女作家的八部短篇小說》。1967年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所出的《中國現(xiàn)代中短篇小說選》英譯《金鎖記》(The Golden Cangue)。宋淇認為,張愛玲中英文“也真拿得出去”,自譯時不管是中譯英還是英譯中,“二者同樣地自然,看不出翻譯的痕跡”。宋先生還提到,夏濟安和夏志清對她這種隨心所欲、中英文互譯的本領(lǐng)很是欽佩。《五四遺事》寄到《文學雜志》去發(fā)表時,夏濟安說完全看不出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除了一時疏忽,把女主角‘范小姐’寫成‘方小姐’之外”。
此外,她還改編或節(jié)譯過《魂歸離恨天》、《一曲難忘》、《荻村傳》、《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瑪曲昂娜的家》等。其中前兩部是為香港電懋公司改編的劇本,后三部是為美國之音改編的連續(xù)廣播劇。
1967年張愛玲獲得麻州劍橋瑞克利夫研究院基金資助,得以實現(xiàn)自己的夙愿,開始英譯《海上花列傳》(又稱《海上花》)。《海上花列傳》是韓邦慶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長達40多萬字的吳方言小說。對古典小說最博學多才且評價最嚴的魯迅不僅在《中國小說史略》將其列為清“狹邪小說”壓卷之作,還稱贊它“平淡而近自然”。胡適對這部小說也極為推崇,稱其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張愛玲更是認為它代表了中國文學“平演而近自然”的最高理想。張愛玲花了十余年,先后將其譯為英語本《海上花列傳》和國語注譯本《海上花列傳》。分屬語際翻譯和語內(nèi)翻譯,是翻譯史上罕見的現(xiàn)象。前者將《海上花列傳》推向世界文學殿堂,使異質(zhì)文化讀者有可能親近中國文學,感受中國風塵女子的悲歡離合和愛恨情仇。后者不僅為研究者了解這部吳方言小說提供了便利,也大大推動了一般中文讀者閱讀和欣賞這部小說的熱情和積極性。
1982年《海上花列傳》第一、二章的英譯應(yīng)邀發(fā)表于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辦的《譯叢》通俗小說特大號。國語注譯本《海上花列傳》于1983年由皇冠出版社正式出版。英譯本《海上花列傳》雖完成在國語本之前,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出版社,80年代中期張愛玲寓所不幸遭竊,丟失的物品中就包括這珍貴的英譯《海上花列傳》定稿。直到2002年,張愛玲遺物中的部分手稿被轉(zhuǎn)交給著名香港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孔慧怡整理潤色,英譯《海上花列傳》才得以在2005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孔慧怡在跋中介紹,交給她的手稿不僅不全,而且是初稿,不清楚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很多,她差點放棄,不過因為她自己倡導合作翻譯,才堅持下來。由于張愛玲對原著了解深刻,譯作結(jié)構(gòu)上的變化(包括刪節(jié)和對個別地方的改寫)保留了張愛玲的處理,但在全書的翻譯方法、語言應(yīng)用和節(jié)奏,乃至于人名翻譯方面,可以說40%為張愛玲的工作,60%為孔慧怡的努力。
上一篇:著名翻譯家王永年:中西文學的信使
下一篇:論中國翻譯的文化戰(zhàn)略